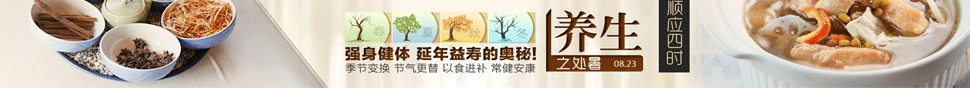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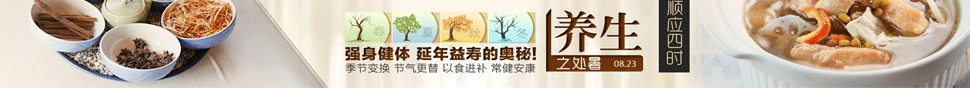
偶见某公知雄文,大赞某酱香型白酒时,不忘用“垃圾浓香”四字,以示对浓香型的蔑视。仿佛把别人贬的越低,自己就越高贵似的。
很像无赖撒泼,有点理的话,他得理不让人,曰“咱有理讲理”;若他没理,他就骂街,一骂三分理,气势要上去。他相信只要骂声洪亮,就会获得支持。
这风格还真能吸引不少眼球。普罗大众谁不爱热闹呢,哪怕半夜里听到高声喧哗,再睏都得爬起来,躲在窗帘后头,支起耳朵睁大眼睛,不放过任何的风吹草动,谁是谁非不关心,就图个消遣。
所以人家脏口一开,就动辄多少万的阅读量,真有指点江山的意思。小庙发文阅读量不高,跟人家不在一个等量级,几位时常转发的酒友,小庙都无比珍惜地用小本本记下来,他日江湖相见定要敬酒三杯。咱们影响力有限,在此闲言碎语,不过是背后发虚而已。
既然背后发虚,也就不必忌口,小庙以为,这位“公知”活脱似一只“茅贼”。小庙亦曾访仁怀,遇见的都是谦谦君子,如“茅贼”者绝无仅有也。它可能茅台镇都没去过,只是听闻厂家宣传,就以为自己融会贯通了。这般货色要是活在一百多年前,练上三天二踢脚,真的会相信自己刀枪不入呢。
小庙本不想驳他,原本传统白酒就不分香型,“白酒在味不在香”,以香型而论白酒极其无聊。但谈兴已起,欲罢不能,索性借机捋一下,他口中神秘莫测的那些都是什么。
论起酱香型白酒,就必须从茅台谈起,说好说坏,茅台可能并不关心,往往得罪的是其他人。茅台酒和酱香型白酒之间,关系微妙,你若对酱香型语出不敬,他们指责你说“你竟敢污蔑茅台”;而你若给茅台点赞,他们比着大拇指说酱香型就是好,好像所有的酱香型都是茅台似的。咱干脆说清楚,只是说茅台!跟其他酱香型没关系。
谈茅台,就绕不开“生产工艺最难”这个梗。每当谈到品质,他们总爱说这句“酱香型的生产工艺最难”,然后意味深长的看着你,等你自己下结论。言下之意是,只要生产工艺最难,品质就一定会好。
工艺难的,品质就一定好吗?小庙不敢苟同。我觉得回锅肉的工艺比清炖燕窝难,但我从不认为回锅肉就比清炖燕窝好,并不是谁难谁就优秀。
你看考得上北大清华的,几乎都不觉得学习难,“难者不会,会者不难”嘛。当然,被学习难住的也不是全不优秀,只不过后来都跟小庙差不多,几十年过去,还在人海里浮沉呢。当初吃不了学习的苦,到如今什么苦都得吃。挣钱比马云难多了,可也没觉得自己比杰克优秀。一盘烂肉岂敢藐视燕窝,实力不允许。
况且,回锅肉也并不是真的难,它其实是繁琐。“繁琐”这个词很贴切,更接近真相,咱们不能以为,繁琐的就是难的。
比如说,炒鸡蛋比煮荷包蛋繁琐,但要说难度系数,荷包蛋难度更大。能煮出完整荷包蛋,一点蛋清都不散的,一百人里找不出一两位来。难易与否,不在于工序繁琐或简单,繁琐的未必难,简单的也未必容易。
“难”是什么呢?好比让你命题作文,你不会写,抓耳挠腮写不出来叫做难;什么是繁琐呢?殚精竭虑把作文写完了,老师让你再从头抄一遍,这叫繁琐。厨子若把繁琐当成难,一脸严肃的告诉咱们“回锅肉工艺最难”,那指定不是炒菜的厨子,而是炒作的厨子。
所以哪怕茅台是繁琐的,也不代表就是难的,何况茅台也并非我们以为的那样繁琐。对茅台的误解,多是从“四高两长一大一多”、“”开始,因为表述方式过于抽象,使我们理解起来很吃力。好比懒汉长了一张巧嘴,活没干多少,诉起苦来跟天底下就他功劳大似的。
但咱们能体谅厂家,大把的银子花出去,当然要用来夸自己,天经地义。然而咱们却不能把宣传材料当教材,不然越学越糊涂。
学校老师传道受业解惑,要求深入浅出,怎么便于学生理解怎么讲,三言两语能把复杂的问题讲明白的,才是名师。可酒厂的宣传正好相反,要把简单的问题搞复杂,目的不为让你理解,而是要让你觉得他厉害,特别的厉害。
不过呢,虽巧言令色,言过其实,但酒确实是好酒,茅台的品控,放眼四海无出其右,咱们并不是在说茅台坏话,而是试图了解传闻里的那些,真相究竟是什么。
例如“四高两长一大一多”,这段话出现的时间并不太久,究其根源,要追溯到年6月23日,这一天在北京总政招待所,召开了全国酱香型白酒风格质量研讨会,主持人是白酒协会秘书长辛海庭,参会的有方心芳、周恒刚、熊子书、季克良等。
研讨者,研究、讨论也。为什么要研讨呢?肯定是有了大的进步,新的成果,才会召集大家一起研讨。主办者劳心费神的办会议,定然不是要开展自我批评,更不是要听别人批评自己。虽说批评就是帮助,但该帮助的早帮助过了,不会留到研讨会上才帮助。若会下不帮助,会上才帮助,那就不是帮助了,那是发难、是拆台,谁不明白这个道理呢。
就是在这次会议上,首次提出了“四高一长”,这是对酱香型白酒工艺的概括、总结。这个提法在后来三十年中,不断增加补充,最终形成现在的“四高两长一大一多”:高温制曲、高温堆积、高温发酵、高温馏酒、生产周期长、储存时间长,大用曲量、多轮次取酒。
“四高两长一大一多”,是概括,是总结,从来都不是秘密,外行看起来神秘莫测,内行看起来轻描淡写。
所谓高温制曲,若要酱香型,就必须要高温制曲,没有高温酒曲就做不成酱香型白酒。同样,没有中温酒曲也做不来浓香,没有低温酒曲也做不出清香,做什么酒用什么曲。在酒曲的制作过程中,高温、中温、低温,都要控温,并不是说“高温酒曲”里面有个“高”字,它就比别的酒曲高明了。
好比杂酱面用黄酱,炸酱面则用面酱,黄酱和面酱是两种不同的酱,它们并没有高低分别,就不能放在一起做比较。哪种面更好吃,要看厨子的手艺,食客的偏好。不能因为爱吃杂酱面,就吧唧着嘴夸黄酱是世界上最好的酱。
所以说高温曲跟中温曲、低温曲以及其他曲,各有其特点,不存在谁比谁更好。若非要比出个高低,得各自跟同行比,茅台的酒曲要跟其他酱香型比,才能分出高下来。小庙视野有限,目之所及,茅台的酒曲在酱香型白酒中是最好的,夸张的说“没有之一”都不算过分,但只限在高温曲中做对比,不能广而化之,喻为是所有白酒中最好的,则严重失实。
虽然茅台的高温酒曲做的好,可是把它神奇化也不对,比如说“踩曲”,曲不仅要踩,还得年轻女子去踩,说是自古就有的传统技艺。
小庙孤陋寡闻,窃以为这若真是传统技艺,那可太难为古人了,在盛行“缠足”“束胸”两大陋习的古代中国,找大脚板的姑娘去踩曲,可不是件容易事。
当然,踩曲本身没问题,问题在于,是否必须女人去踩曲?茅台酿酒又是否全用女人踩的曲?真相是什么,耐心寻访亦可见蛛丝马迹。
今天是年9月9日,打开茅台集团官方网站首页,“文化茅台”一栏里,点开“传奇茅台”的类别,第七篇文章标题为《茅台酒质量进一步提高》,在这篇文章里,茅台说“那时,地主、资本家住在洋楼上花天酒地,哀叹“人生几何”。工人们则在地狱般的厂房里从事笨重的体力劳动。现在,工人们还把联合机械化制曲叫做“踩曲”。曲,果真是踩成的吗?是的。解放前工人给资本家制曲全靠用双脚来踩,即使是身体健壮的年轻人,踩上半小时的曲,就会累得满身大汗,不知有多少人因劳累过度而死去。”
诸君,非是小庙编纂,此乃茅台
本文编辑:佚名
转载请注明出地址 http://www.piantoutongazl.com/ttzmb/12764.html


